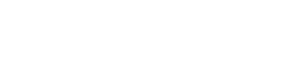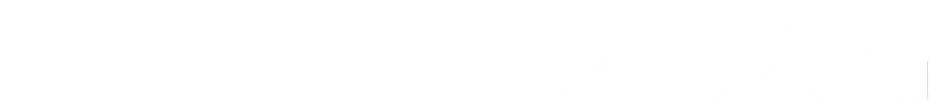文/梁君度
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經洞裏,公元868年的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卷首圖以其精湛的刀痕,無聲訴説着早期雕版印刷的輝煌,成為世界公認的木刻版畫珍品。這幅作品,連同漢代畫像磚的樸拙遺韻,直至當代數字版畫的絢爛光影,共同勾勒出一條獨特的藝術軌跡——中國版畫藝術。它始終以鋒刃在中華文明的浩瀚長卷上,鐫刻下深刻的精神印記與時代回️響。
梳理中國版畫藝術的發展脈絡可知,中國版畫的源頭可追溯至古老的契刻傳統。商周青銅器上威嚴神秘的饕餮紋飾,已暗含版畫“凸版”原理的雛形。早期雕版印刷的典範,如唐代《陀羅尼經咒》與前述《金剛經》卷首圖,標誌着版畫技術的成熟。這些作品不僅承載着佛教思想的傳播,其線條的韻律與流暢性,更與同時代敦煌壁畫中飛天的飄逸姿態形成了跨越媒介的藝術對話,奠定了中國版畫以線造型、注重神韻的美學基礎。
至宋代,版畫的應用領域與技術理性顯著提升。1103年,北宋的《營造法式》作為建築鉅著,其插圖藝術具有里程碑意義。李誡所記錄的“界畫”技法,通過精密的平行線條刻劃,將複雜的建築結構與美學理念轉化為清晰可複製的視覺圖譜。這種“以刀代筆”的精確表達,為後世《清明上河圖》式宏大市井敍事的版畫再現提供了技術支撐,使版畫從宗教領域拓展至科技、文化傳播,成為名副其實的“圖像活字印刷術”。
中國版畫藝術的現代轉型,始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魯迅先生倡導的新興木刻運動。這絕非傳統版畫的簡單延續,而是一場深刻的文化啓蒙。1931年魯迅在上海創辦木刻講習班,引入凱綏·珂勒惠支等藝術家的作品,倡導“力之美”。他將自身在《野草》中的哲學沉思與批判精神,灌注於木刻藝術,賦予其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屬性,點燃了文化暗夜中的火種。
隨着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,木刻版畫因其製作便捷、傳播迅速的特性,成為最具戰鬥力的藝術形式,“抗日木刻”運動由此勃興。青年版畫家們以刀為槍,創作了大批抗戰版畫,這些作品成為革命現實主義藝術的典範,通過街頭展覽,通過《新華日報》等媒體廣泛傳播,形成“刀筆勝千軍”的磅礴文化抗戰景觀。
新中國成立後,版畫藝術迎來新的發展契機。在版畫家思想解放、探索新風格技巧的浪潮中,黃永玉於1956年創作的《阿詩瑪》組畫,標誌着中國版畫藝術現代性轉型的一座高峯,具有里程碑意義。黃永玉深入雲南採風,將撒尼族口傳敍事長詩《阿詩瑪》中的人物傳奇與地域風情,以獨特的木刻語言進行視覺再造。其作品線條奔放流暢,充滿韻律感;構圖新穎大膽,極具裝飾性;人物形象生動傳神,洋溢着濃郁的民族氣息。尤為重要的是,《阿詩瑪》組畫成功實現了民族化與國際化視野的辯證統一。它既深刻汲取了雲南民間藝術的精華(如服飾紋樣、傳説意象),又融合了德國表現主義木刻的強烈形式感與刀法張力。黃永玉此舉,極大地拓展了版畫的表現疆域,使其成功突破了單一作為“革命鬥爭工具”的侷限,昇華為承載民族集體記憶、探索個體情感與形式美學的“視覺史詩”,為新中國版畫注入了強勁的現代活力,並深遠影響了後續藝術家的創作路徑。
進入信息時代,中國版畫藝術展現出前所未有的開放性與實驗性,呈現出多元生態。藝術家們積極擁抱新材料、新技術、新觀念,使版畫的邊界不斷拓展。這一過程顛覆了傳統版畫的“印痕”概念,將“製版”行為轉化為空間裝置的營造,將宋代郭熙提出的“高遠法”空間觀解構並重構於光影與現成品之中,實現了傳統美學精神的當代轉化。強烈的色彩對比與充滿生命張力的形態,使古老的題材獲得了極具現代性的色域繪畫表達,展現了傳統基因在當代語境下的旺盛生命力。
中國版畫通過一代一代版畫家的努力,將繼續以其獨特的語言,在時間的河床上刻下屬於這個時代、並通向未來的文明印記。